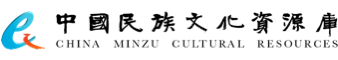
当前,流动性已成为全球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广泛的互动中,人们不断跨越各种边界,人们的认同亦具有了多样性和流动性。跨界民族恰恰处于这一流动性的显著地带。如何探讨边界、认同和跨界民族的发展问题?8月18日,由延边大学、吉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跨界民族专业委员会、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五届跨界民族论坛在延边大学举办。延边大学党委书记金雄、吉林省民委专职委员金惠淑等领导在开幕式上致辞。来自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民委、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云南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韩国釜庆大学等36所高校、研究机构的6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边界、认同与跨界民族发展”的主题展开了研讨。
“跨界”成为人类学民族学的核心议题
当今,跨界研究已成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的核心议题之一,也必将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提出新理论、在国际学界形成中国话语的重要突破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麻国庆提出“跨界、流动与跨区域社会”的议题,在当代世界体系复杂的交叉互动中,展望中国人类学的跨区域研究。他认为中国人类学的新理论有可能出自东南亚、南亚、东北亚、中亚等过渡地带。交错地带与跨国社会领域、通道与圈域、区域亚洲、文化中国与世界单位等概念将会成为跨区域社会体系的研究基础。
在此视阈中,麻国庆集中思考华南在全球社会的地位,以及华南与东南亚社会的联动性问题。他主张跳出民族国家的限制,突破传统的大陆视角,不仅从区域的角度审视华南,更进一步从“海域意识”出发来思考华南到东南亚这片区域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他认为跨区域社会体系是跨越了家族、社区、族群、民族、国家与跨国家区域等不同层次的社会单位,是全球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愿景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邴正同样关注区域研究,他将东北文化视为一个文化多元复合体。他认为东北文化是东北四大族系之间、东北地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之间、东北文化与东北亚文化三重文化圈交叉重叠的复合产物。从历史上到现在,生活在东北区域的朝鲜族、俄罗斯族和蒙古族三个跨界民族对东北文化的多元复合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对于我国的西南边疆,云南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荣将直过民族与跨界民族相关联,讨论了民族研究的价值和使命,结合“一带一路”建设,探讨了如何通过民族团结进步创建,逐渐推进直过民族、跨界民族实现从血缘认同向地缘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转化。他着重展示了云南民族大学多种措施并举,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实践与探索。
迁移中的认同困境
跨界、认同往往与人群的迁徙相关联。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关于流动性与迁徙族群的讨论中,悲情的“离散”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研究的一个全球性议题。而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开始关注与“离散”相对应的“回归”概念。论坛上,多位学者的发言关涉到跨界者、迁徙者的“回归”,涉及“回归”的理论、动因、认同、国家安全等议题。
什么是“离散”?什么是“回归”?涉及哪些理论讨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教授周建新基于在西藏自治区察隅县西托拉卡村——“缅甸村”的田野调查,以藏族老人伍金扎西亲历的两次重大人生选择微观呈现了这一理论问题。
1945年,39岁的穷苦人伍金扎西孤身逃到缅甸,41年后的1986年,他带着一个26人的大家庭回归故土。周建新分析了这两次选择的动因,最初的离散是要逃离旧西藏政府黑暗的农奴制度和残酷的阶级压迫,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周建新认为,传统意义的离散故事似乎都包含“避害”因素,但“回归”不一定是“驱利”的。针对当今学界把推拉作用下的“本土—海外—本土”迁移路线的跨国移民群体视为回归群体,他认为,离散和回归蕴含着在民族国家体系下的人类生存逻辑,“回归”不同于利益驱动的近现代移民现象,难以用移民“推拉理论”解释。在伍金扎西的人生故事里,回归的选择是一种对故乡、民族、国家及未来的主动的认同性选择。
与会学者在讨论中,还将朝鲜族跨国流动的现象与当前学界的“回归”理论进行关联、对照。改革开放、中韩建交以来,我国朝鲜族大规模去韩国打工。尤其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大量的朝鲜族去了韩国。但是,这种由利益驱动的大规模民间跨国流动并非是与“离散”相对应的“回归”。
这一流动过程产生哪些认同困境和发展问题?这一议题是延边大学多年举办跨界民族论坛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关照和理论关照。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李梅花讨论了朝鲜族跨国流动中的边界、认同与发展。在韩朝鲜族在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更遭遇了韩国社会的隐形排斥和深度区隔,在某些人想象的“故国”中处处体会着异乡感。李梅花认为这些遭遇坚定了他们对祖国的国家认同,但跨国体验又使其认同呈现出多重性、可变性和敏感性。同时,长期经济驱动的单向跨国流动造成了边境乡村的空心化,为朝鲜族社会带来了发展的困惑和隐患。
在研讨中,延边大学民族研究院院长朴今海指出,近几年朝鲜族跨国流动中出现了从单一的劳务输出走向多元化流动的新动向,她主张学者在强调政治认同之外,关注跨界民族人口流动的类型、性质的差异性与多样性,正视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认同分化现象。
历史叙述与认同建构
群体的边界往往在互动中得以形成,而历史叙述是人们构建群体边界和认同的重要维度。此间,认同既是互动的产物,又是确认边界的重要因素。当关涉到跨界民族,这一议题则更具复杂性和现实性。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副院长李晓斌认为,云南部分跨界民族历史叙述的复线式建构将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认同、国家认同产生影响。在云南的17个跨界民族中,有部分跨界民族的主体分布于国外,如佤族、傣族、德昂族等。随着民族国家的构建,这部分跨界民族在国外的主体部分出现重构历史的状况。例如,缅甸的德昂族在历史的大部分阶段与中国王朝国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缅甸的德昂族的历史发生了重构,开始强调与缅族相似的迁徙史、强化与孟族一起参与缅甸历史的过程、突出与东部孟高棉文化的共同性,以此来淡化历史上中国带来的影响,强化缅甸的德昂族对缅甸的历史归属感,增强对缅甸的国家认同。李晓斌因此建议“一带一路”的建设应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影响,重视和发挥好跨界民族的桥梁作用。
跨界与发展——一个还需充分讨论的议题
相关学者已经意识到边界本身的流动性和多样性;边界亦非边陲和边缘,恰恰意味着机会和机遇;同时,边界也不必然带来认同问题。我国的30多个跨界民族在加强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经贸往来与合作、政策沟通了解方面具有重大优势,特别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跨界民族的研究也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进行学科建设、提高国际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契机。
学者们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讨论跨界民族的发展,涉及到多元文化发展、教育发展、语言发展、公法规制、大学生社会融入等议题。其中,兰州大学中国边疆安全研究中心教授徐黎丽梳理了中蒙边境口岸的共性特点和发展问题。15个口岸横跨内蒙古自治区、甘肃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三省、自治区之间的口岸建设反差大,缺乏联动合作,口岸本身缺乏文化交流与理解功能。徐黎丽建议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契机中处理好生态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建立三省、自治区联动机制,保持东部和西部口岸平衡动态发展和各口岸特色建设,重视口岸与所在乡镇间的互融共生,同时在国家层面进一步促进中蒙关系的友好发展。
此次论坛上,主办方还特意讨论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议题,如裕固族的教育发展、达斡尔族的萨满教传承等。
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在跨界民族的发展中的确存在诸多困惑,有待深入研究。
此次论坛上,主办方和多位参加过历届跨界民族论坛的专家学者都深有感触,近几年我国人类学民族学界在跨界民族研究领域已开辟了大量的研究路径,也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和成果。更重要的是,大量年轻学者正行走在跨界民族研究的田野中。当前,“一带一路”建设正需要人类学民族学跨界研究有所作为,开展人类学民族学界大规模的协同研究正是其时。